一
對方已經進入了燠熱的蟬聲
自石級下仰視,危危闊葉樹
張開便是風的床褥──
巨礮生銹。而我不知如何於
硝煙疾走的歷史中冷靜蹂躪
她那一襲藍花的新衣服
有一份燦爛極令我欣喜
若歐洲的長劍斗膽挑破
巔倒的胸襟。我們拾級而上
鼓在軍中響,而當我
解開她那一排十二隻鈕扣時
我發覺迎人的仍是熟悉
涼爽的乳房印證一顆痣
敵船在海面整隊
我們流汗避雨
二
敵船在積極預備拂曉的攻擊
我們流汗佈署防禦
兩隻枕頭築成一座礮臺
蟬聲漸漸消滅,亞熱帶的風
鼓盪成波動的床褥
你本是來自他鄉的水獸
如此光滑如此潔淨
你的四肢比我們修長
你的口音彷彿也是清脆的
是女牆崩落時求救的呼喊
彷彿也是枯井的虛假
我俯身時總聽到你
空洞的回聲不斷
三
巨礮生銹,硝煙在
歷史的斷簡裏飛逝
而我撫弄你的腰身苦惱
這一排綠油油的闊葉樹又在
等候我躺下慢慢命名
自塔樓的位置視之
那是你傾斜的項鍊一串
每一顆珍珠是一次戰鬥
樹上佈滿火併的槍眼
動人的荷蘭在我硝煙的
懷抱裏滾動如風車
四
默默數着慢慢解開
那一襲新衣的十二隻鈕扣
在熱蘭遮城,姐妹共穿
夏天易落的衣裳:風從海峽來
並且撩撥著掀開的蝴蝶領
我想發現的是一組香料羣島啊,誰知
迎面升起的仍然只是嗜血的有着
一種薄荷氣味的乳房。伊拉
福爾摩莎,我來了仰臥在
你涼快的風的床褥上。伊拉
福爾摩莎,我自遠方來殖民
但我已屈服。伊拉
福爾摩莎。伊拉
福爾摩莎
--
美術設計:許宸碩
攝影來源:Flickr c.c.|思弦 張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mall_0323/2604477549/ ),原圖套用濾鏡後加上文字及Logo,以CC BY方式分享(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
--
◎小編利文祺賞析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開始殖民台灣,並於台南開始建造熱蘭遮城,該城耗費十年建立。在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進攻台灣,和荷蘭人短兵相接,這段明鄭和荷蘭的戰爭,即是楊牧〈熱蘭遮城〉的背景。
詩中的敘述者「我」為抵禦明鄭的荷蘭人,眼看「對方」進入燠熱的台灣,「流汗佈署防禦」,當中國的「敵船在積極預備拂曉的攻擊」。然而,不管是明鄭或荷蘭,都是殖民暴力,差別在於不同形式的外邦統治罷了。因此,詩人將殖民者/被殖民者,形容為男性/女性,也就是說,將殖民議題,以性暴力為隱喻。如:「硝煙疾走的歷史中冷靜蹂躪/她那一襲藍花的新衣服」,「以歐洲長劍斗膽挑破/巔倒的胸襟」,或是「解開她那一排十二隻鈕扣時」。抗拒的鈕扣、展現的乳房、修長的四肢、清脆的亞洲風味口音、被強暴,這些意象暗示了歷史中台灣被蹂躪,任人宰割的處境。
荷蘭人在詩末提到:「我想發現的是一組香料羣島啊,誰知/迎面升起的仍然只是嗜血的有着/一種薄荷氣味的乳房」,亦即為原本以為是香料天堂,卻不知在此也有戰火,這是一種美與致命的所在。然而,他完全地屈服於台灣的美,「我自遠方來殖民/但我已屈服」,並開始呼喚台灣的最早的名稱:「伊拉・福爾摩莎」。這也或許是楊牧認識台灣歷史後所要彰顯的,作為「他者」(the Other)的台灣,如何包容,使所有的暴力、征服,最後在作為「他者」的台灣中消解,純粹地領悟到台灣的崇高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Lisa Wong認為,在台灣的當代語境,「福爾摩莎」之名具有歷史性,試圖擺脫中國性Chinese-ness,並隱含了台灣性Taiwanese-ness(p. 148)。這或許提示了楊牧的後殖民心境,並提倡台灣的主體,和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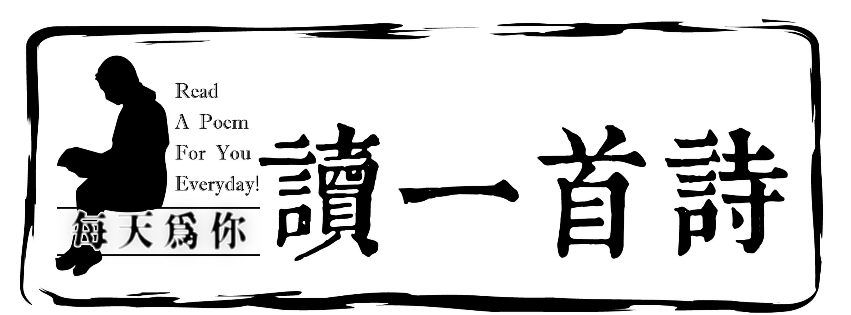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