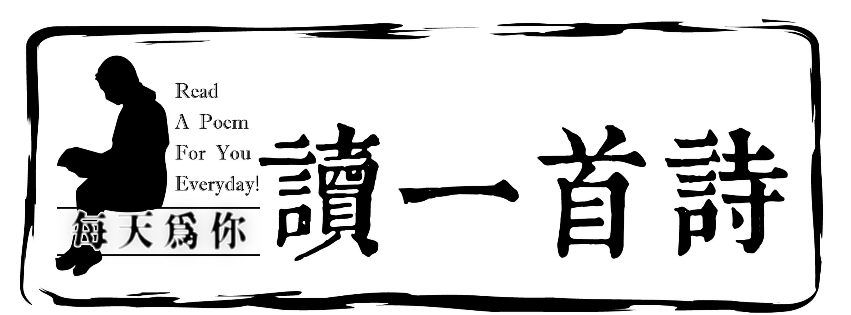傷停時間 ◎林宇軒
2023年10月25日 星期三
傷停時間 ◎林宇軒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偏不主義 ◎胡玖洲
▍新詩集分享:胡玖洲《我們在房裡看A片》 #臉書文末抽書
偏不主義 ◎胡玖洲
我偏不愛美式咖啡,不愛精煉的話語
不愛夕陽的餘暉而偏愛一無所獲的日子
明天該很好,若所有偶然都在場
每顆流星都無處可躲地,落在我的眼睛
但我偏不著急,呆坐窗前
等候每個感覺的雛形,冉冉升起
偶爾你來,穿著白色連衣裙
連結愛與赫茲,調整詩的頻率
讓所有貧瘠的基因都學會了飛行
如果不來,我也能看麥子收割成黃昏
聽大風拂過麥浪,如不斷癱倒的多米諾骨牌
露出每個精心編排的劇情,偏不承認
等待也可以是件美好的事情
假如你來,倘若明天,你會來
但又或許明天並不來臨
時間也偏不懷疑,時針停在七點
還尚未盛開的花季
而我愉悅地繼續,掌握自己的節奏
像一隻俏皮的精靈,在停滯的時間裡跳
一個人的舞曲,反復排練我的
偏不主義。偏不帶著鮮花
偏不跳華爾茲,偏不決定在今天
大聲朗讀你年少的詩句
令你羞澀,慌亂,如明天待嫁的新娘
在大庭廣眾下說愛你,哦不,我偏不
我們不能一起愉快地變老,一起揮霍
滿天繁星的假日,坐在床邊,偏不完整地
在你耳邊唸完每段聽來的愛情
偏不將彼此的誓言牢牢緊靠成一枚鑽戒
直到時間在我們的生命,誕生出
新的意義
我偏不決定,將愛進行到底
或許明天,我們偏不甦醒,偏不撕下日曆
不斷在日出之前銜接昨日的風景
整夜窩在房間成為與貓遊戲的貓貓奴隸
看貓在懷裡垂釣,魚的陰影,那麼
虛度的時間是否也會被馴養出
糖果的甜蜜。但我偏不
偏不血本無歸地,將一百分的喜歡
都放進一個人的口袋裡
讓視線填滿一個人的眼睛
就讓我們逗留在彼此的脈搏,習慣一種
超現實敲打樂迷幻舞曲不斷衝擊
初開的情慾,一如回到每個邂逅的場景
哪怕猶豫,迷離,偏不一錯再錯地
將情書毫無保留郵遞。將一半
寫在手心,偏不歉意,偏不答應
你是此刻所有喜悅的心情
今夜,我決定偏不愛你
◎作者簡介
胡玖洲,97年生於南國,現居臺北。曾任職於馬華文學館,同時兼任《蕉風》文學雜誌編輯,目前就讀於臺大中文系研究所。2023年10月出版詩集《我們在房裡看A片》(有人出版社)。
◎小編 #樂達 賞析
嫁接各種看似矛盾的元素,操演豐富的句式鋪演成詩,這次小編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新世代的馬華詩人―― #胡玖洲 。「元宇宙」和「觀音嬤」、疫情和情慾上的「安全日」……,正如唐捐在序文中談到,玖洲嫻熟於雙線交織,看似奇異、卻又巧妙而自然地勾連起許多異質事物;又如每詩粉專在2021年12月8日分享過他的得獎作〈我們在房裡看A片〉,偷看A片的日常片影和磨練詩藝的孤獨時分,在他靈活的長句鋪展中交織不離。正逢玖洲新詩集出版,今晚小編則來分享另一首詩〈偏不主義〉,看看他如何經營一個傲嬌者的口吻,來述說愛戀時的複雜心理,順便談談詩人的其他特色。
一如玖洲〈遠方的戰爭〉援引並解構了余光中詩〈如果遠方有戰爭〉,從中延伸出新意;這首詩或許也取材於辛波絲卡的〈種種可能〉――只是當辛奶奶「偏愛」種種零碎卻構成自我與生活的事物時,玖洲反其道而行,結合多變句式和韻律安排,反覆倡行那「偏不主義」,否認(或只是拒絕承認)種種愛戀的可能與事實。整首詩的發話者「我」從一開始,便藉由對事物的否定來經營某種自我姿態,彷彿自己拒絕被那些日常、甚至可能美好的事物(如「夕陽的餘暉」)所定義,拒之門外、切斷聯繫;而且比起單純否定,「偏不」的微妙語感,也為某種複雜而固執的性格奠定基調(儼然存在一個對象,而「我」偏偏不要依循他或多數人預期的走向)。就像隨後「流星」落入雙眼的假想情境中,看似「我」正揣想著心願實現的可能,讀到此處的我們可能也期待「我」如何由此發展下去時,緊接而來的「但我偏不著急」卻又迅速打消預期,並從中帶出「我」願意為「等候」而耐心堅持著。從等候「每個感覺的雛形」到「你」的出現,漸漸讓愛戀中人的心理作為主題浮現出來,而且也深化了「我」的矛盾性格――你來也好、不來也罷,我都能享受在等待的每個美好當下,卻又口是心非地「偏不承認」這份事實。
其後,連接前後兩節的橋樑句「假如你來,倘若明天,你會來」,一方面透露並加強表現出內心祕而不宣的真實盼望(從期待「你來」到進一步你「明天」就會來),另一方面,也回扣到某種矛盾――「我」不斷地履行「偏不」,卻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像一些「假設」情境(詩中的「你」也頻繁出沒於此),口口聲稱的「偏不主義」似乎越來越無法約束內心的情感。看似標榜出一個能「掌握自己的節奏」、不假外求的自足個體,卻又在「否認」的免死金牌下,益加張揚心中對「你」的澎湃熱情。大聲朗讀詩句、大膽地說愛你、攜手共度甜蜜美好而堅定的一生……,這些根本都還沒實現,但就像第一節寫到的,「每個精心編排的劇情」(戀愛時的各種小劇場),背後都因為「偏不主義」的一概否定,才能一概被容許。我能逐漸無拘無束而「合法」地戀慕、幻想、吐露心聲,只要我不要承認喜歡你、愛你的事實就好,一如第二個橋樑句所拒絕的「將愛進行到底」。
很有意思的是,來到整首詩的最後一大節,「偏不主義」又深化出更進一步的意義。前面不斷藉由「假想」來實現我與你的愛情,並特別強調自己能「愉悅地繼續」跳一個人的舞曲,隱隱約約透露出這分愛戀(至少在此刻)的困境,並在這節裡逐步彰顯出來。在一切心願成真或落空的「明天」到來之前(明天你可能會來,也可能又不會),種種試著延緩明天到來、延長今夜喜悅的行為,雖名為「我們」所做,卻又何嘗不是「我」的真正寫照呢?從假想回到現實,真正的我或許正在「虛度的時間」中感受到愛意逐漸變濃,卻也明白如此的危險性――「血本無歸地,將一百分的喜歡/都放進一個人的口袋裡」,愛得越深、自己越依賴對方,萬一結束時也將失去越多――為了不讓它有天成真,「今晚,我決定偏不愛你」。換言之,「偏不主義」彷彿是保護自我不受傷害的機制,然而,它也默默容許著愛意的漫漶(「你是此刻所有喜悅的心情」)。
如此矛盾、曲折的情結,隨著一路以來的情感堆疊,推進至亮眼的最後一句到達高峰――口非而心是,既害怕失敗、又盼望實現,既依戀對方、卻又希望維護住一定的自我,「偏不主義」巧妙詮釋、重現、也接納了這種愛戀中弔詭卻又極其自然的心理,並在斷定出心願實現與否的「明天」之前,讓充滿假想、前途未知渺茫的「等待」,持續成為可能。綜觀整首詩,詩人透過句式多變的長句和語意上的轉折、矛盾,營造出戀愛中人的複雜心跡(愛情的當下絕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同時經由韻律上的經營(像是可以先觀察這首詩的尾韻),讓通篇讀來順暢,不因語句繁多而無以為繼。凡此,皆充分展現出這位詩人令人矚目的起手式。
▌抽獎辦法:(請到臉書粉專)
1.
按讚這篇貼文
2.
tag三位朋友並隨意留言(自由分享貼文)
抽獎活動至10/29晚上23:59截止,我們將抽出2位幸運讀者,各贈送《我們在房裡看A片》一本。
#購書連結請看留言!
---
文字編輯:樂達
美術設計:EJ
#胡玖洲 #偏不主義 #我們在房裡看A片 #馬華詩
2023年10月14日 星期六
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 ◎阿萊杭德娜・皮札尼克 Alejandra Pizarnik(譯者:汪天艾)
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 ◎阿萊杭德娜・皮札尼克 Alejandra Pizarnik (譯者:汪天艾)
致瑪莎・伊莎貝爾・莫伊阿
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
死亡的童年的夢中的詞語
那從來不是我想說的
原生的舌頭割斷
舌頭是一個認知器官認知
所有的詩的失敗
被自己的舌頭割斷
舌頭是再創造的器官
用於再認知
但它不是用於復活的器官
復活什麽當作否認
我的馬爾多羅的遠方和它的狗
能說的東西裡
沒有任何許諾
能說的等於撒謊
(一切可以說的都是謊言)
剩下的是沉默
只是沉默不存在
不
詞語
做不出愛
做的只有缺席
我說「水」我喝嗎?
我說「麵包」我吃嗎?
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
這個夜晚靜得出奇
靈魂的問題是它看不見
頭腦的問題是它看不見
精神的問題是它看不見
這些密謀的不可見從哪里來?
沒有一個詞語是可見的
陰影
黏著的空間藏著
瘋石
黑暗的長廊
我全都走過
噢你再在我們中間停留一會兒吧!
我的人稱受了傷
我的第一人稱單數
我寫作像一個在黑暗里舉起刀的人
我寫作像說著
絕對的真誠依舊是
不可能的
噢你再在我們中間停留一會兒吧!
詞語的毀損
它們已遷出語言的宮殿
兩腿之間的認知
你把性的天賦怎麽了?
噢我的死人們
我吃了他們我難以下咽
我受不了這樣的受不了了
被遮蓋的詞語
全都滑向
黑色的熔化
馬爾多羅的狗
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
這裡一切都是可能的
除了
詩
我說
知道要說的不是它
總也不是
今天幫幫我寫出那首最可扔棄的詩
那首無用的詩甚至不為
無用
幫幫我寫出詞語
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
◎作者簡介
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本名為Flora,擁有俄羅斯與斯拉夫血統的猶太裔阿根廷詩人,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自幼便罹有長期失眠和各類精神病徵,19歲以Flora Pizarnik為名,出版了第一本詩集《La tierra más ajena\_》(最遙遠的土地),青年時代旅居巴黎,與帕斯、柯塔薩爾等作家往來,曾獲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年度詩歌獎。生前最後幾年因抑鬱症多次出入精神病院,後於1972年吞藥自殺身亡。
如想更進一步認識這名阿根廷女詩人,小編推薦《夜的命名術:皮札尼克詩選》及《皮札尼克:最後的天真》二書,前者收錄了終其一生許多不同階段的詩作,後者則是由阿根廷著名作家塞薩爾・艾拉(César Aira)執筆寫就的傳記,敘述並試圖分析在世人眼中患病早逝的詩人,究竟經歷了哪些可能的追尋、矛盾與掙扎,孕育其詩藝及「阿萊杭德娜」此一人格,乃至於成為20世紀中葉拉美文學史中備受矚目的女詩人。
―
◎小編 #樂達 賞析
今年1月無主題詩選中,小編江豫曾節選、賞析過阿根廷女詩人阿萊杭德娜・皮札尼克(Alejandra Pizarnik)的組詩〈狄安娜之樹〉,談論到許多不離於死亡與幻象的「詞語」如何一再出現於她的詩中,並藉由「狄安娜之樹」此一隱喻,隱然勾勒出自我與詩歌之間的關係(一名隱居在森林的女子,將所有心事、想法以樹木為記)。而這次10月的崩壞詩選,小編想和大家分享她生命最後三年、在世時未及出版的「最後的詩」之一〈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見證一位終其一生對「詞語」和「詩歌」懷有高度檢視與執著的詩人,如何在獨白式的語言中,直陳某種關於語言、信念的崩壞,或者借用塞薩爾・艾拉(César Aira)的話語――「精神和詩學的雙重崩塌」。
在早先許多阿萊杭德娜・皮札尼克的詩作中,可以看見「 #詞語 」始終如影隨形,如〈綠天堂〉一詩便有「珍藏純粹的詞語/去創造新的沉默」,〈啟明人〉中「我的恐懼有詞語,有詩。」,〈毀〉中有「詞語的戰役」等。甚至在詩作之外,詩人也在日常書信及訪談中說道:「我不知道怎麼像正常人一樣說話。我的話聽起來很奇怪,像是來自遠方。」、「我如此努力地對抗我的遲緩,我的沉重,我坐在自己說出的每個詞語上面好像那是一把椅子。」等。雖然我們無法真正明白那些精神疾病與現實中的苦痛,究竟將詩人推向什麼樣的生活,但從諸多詩作和談話中,或許可以推知――對詩人而言,「詞語」本身具備複雜的意義。詩人憑藉詞語(以及連帶的語句)實現她想表達或企及的世界,建構出「阿萊杭德娜・皮札尼克」此一詩人人格呈現於世人面前,並包藏住現實的自己(如塞薩爾・艾拉寫道「包裹著她,像一張不可逾越的網」),然而對她來說,「運用詞語」卻又遠比我們所習以為常的還艱難、艱險許多。詩人不只是「調度」文字的主導者,他同時「對抗」著它們,直到寫下最適切的詞句之前,詩人將要持續在「能指」與「所指」之間不斷掙扎。換言之,「表達」本身其實遠比日常所想的還困難(無論那將成為詩歌抑或「新的沉默」),對於敏銳於詞語的阿萊杭德娜尤為如此。
然而,來到這首〈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繫卻已經斷裂了,詞語「毀損」,甚至,甚至「詩」已經不再能成為可能――這個長久以來賴以存在的事物。如果說,原先作為能指的詞語能夠指向詩人所欲實現的自我,當此際,詩人運用詞語的能力受損、甚至失去對它的信念時,或許也將會連帶讓詩人推向某種無盡的迷失或流亡中,再無任何「詞語」能聯繫、抵達到自我。就像這首詩開頭以來,藉由一系列的否定來宣告目前的狀態――「所有的詩的失敗」,而所有語言的失效卻又源於「被自己的舌頭割斷」。如同「撒謊」般,我已經無法再確切說出什麼了,但是語言之外的「沉默」卻又被詩人所否定,讓自我僅能繼續殘存在謊言或虛話中,無法真正棲身於任何所在,如汪天艾所言「剩下的只有墜落,無盡的墜落,觸不到底的墜落」。
隨後,詩人藉由相似句式的鋪陳累積,一再強化這份語言的失效(「(詞語)做的只有缺席」、「沒有一個詞語是可見的」)。而詞語的不可見,來到第四段又進一步連結到自我的精神狀態。「 #瘋石 」的典故源於中世紀,當時人們認為瘋子額前有「瘋石」,取出那石塊便能治癒瘋病及任何精神疾病;後來阿萊杭德娜也將1968年出版的詩集命名為「 #取出瘋石 」,或許藉以隱喻詩歌與寫作本身。但是在此處,自己已經走過全部「黑暗的長廊」,那塊能治癒一切的「瘋石」卻如同詞語般,不可見,始終藏匿其中。瘋石無法取出,隱然也回應了寫詩的失敗,一如下一段接連所敘述的景況。
詞語的毀損,如「我的人稱受了傷/我的第一人稱單數」所述,也正關乎自我本身。如果無法再實踐寫作,無法表達出誠懇的自己,那不只是「絕對的真誠」會化為虛無,就連自我和詩本身也將如此,如其後寫到「這裡一切都是可能的/除了/詩」。由語言、自我及詩歌共構而成的多重崩壞,推進到最後,促使詩人向這首詩的受訊人(瑪莎・伊莎貝爾・莫伊阿,詩人生前最後的戀人)致上私密而懇切的呼喚/呼救――「幫幫我寫出詞語」,幫幫我重新拾回、救贖我自己。也正是在末段,情感強度累積到高潮,讓人進一步揣想到詩中一再出現的詩題「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的言下之意――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我尚且還能寫出這些(無論能不能稱得上詩)來向你傾吐、呼救;當今夜告退、明天到來,在其他世界其他夜晚,或許就連僅存的所有也將崩壞、永遠失去。
文字編輯:樂達
美術設計:子儀
圖片來源:Freepik
#阿萊杭德娜 #皮札尼克 #Alejandra #Pizarnik #在這個世界這個夜晚 #最後的天真 #阿根廷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