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鈴 ◎楊牧
雨止,風緊,稀薄的陽光
向東南方傾斜,我聽到
輕巧的聲音在屋角穿梭
想像那無非是往昔錯過的用心
在一定的冷漠之後
化為季節雲煙,回歸
驚醒
想像那是記憶
記憶的風鈴
大聲搖過我們的曾經
秋之午後,當陽光試探了
水缸冷暖又將反影投射
天花板上,不斷波動
凝視一張喧嘩澌濺的床
我仰首默數光彩如潮
洶湧,在正上方變化
如暈,如雲,如星隕
依序升沉
如韻
我聽到
鈴聲跌宕過
收穫的瓜園
阻於圍牆,遂反彈到半開的窗前
再不猶豫,飛踴到床上依偎
依偎著通紅的頰。飄零
是髮,是惺忪的眼──
那音樂,這時,充滿了
亢奮的血管,一萬條支流
發源於夢的古潭,上下
頡頏,又一萬條支流
發源於夢的古潭
接觸,匯合
滂沛若洪水
想像那是記憶
記憶的風鈴大聲飄過
我們曾經的
秋之午後
--
◎作者簡介
楊牧(1940年9月6日-2020年3月13日),本名王靖獻,臺灣花蓮人,著名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學者。花蓮中學、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愛荷華大學創作碩士、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親炙徐復觀、陳世驤兩位學人。曾執教於多所大學,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國立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亦曾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並參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創院。
楊牧自中學便矢志新詩創作,並共同主編詩刊。早年筆名「葉珊」,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溢於筆端;1966年赴柏克萊攻讀博士學位,見證六零年代學生運動,三十二歲而改筆名為楊牧,嘗試以詩介入社會。詩文曾譯為多國語語。曾獲時報文學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藝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紐曼華語文學獎蟬獎等。
◎「詩.聲.字」特約撰稿人 賴位政 賞析
第一段:序曲
王國維說「人生過處惟存悔」,愈是看重的,悔恨也特別多。以此觀入,〈風鈴〉不啻是一部斑駁的懺情錄,寫一段「對不起,我曾經愛過你」的自剖。情之所起,自需觸媒,楊牧先用三行喚起興發的瞬刻:
雨止,風緊,稀薄的陽光
向東南方傾斜,我聽到
輕巧的聲音在屋角穿梭
「雨止」預設了兩個前提──主人公必知曾下過雨,同時曉得這場雨在此刻已結束了。「風」、「雨」在詩中常用來隱喻苦難與波折,故「雨止」便像是說:我曾一步一創殘地領受過一段感情,而現在它已成為過去式了。雖然往事早成明日黃花,但「風緊」卻傳達了並未真正放下的事實。「風」可看作情緒的暗喻或是撩動情緒的外力,急吹的風表達了「我的心卻仍不得平靜」。「雨止」(事已了)、「風緊」(心未平)乃拉開了最初的張力。自然物象賡續發展,由「雨」、「風」過渡至「稀薄的陽光」,一個魔幻經驗就此迸現:「我聽到/輕巧的聲音在屋角穿梭」,從光到聲,視覺轉聽覺的模式,烘托了詩題「風鈴」。在「風鈴」二字尚未正式登場前,楊牧先定義這聲音:
想像那無非是往昔錯過的用心
「往昔」曾「用心」過,但終究「錯過」,不禁讓人好奇這裡頭究竟有何銘心刻骨、陽差陰錯?「往昔」、「錯過」,故曰「止」; 因「用心」,所以「緊」,結構呼應精巧。次三行黏合甚嚴,宜與此行一氣貫讀:
在一定的冷漠之後
化為季節雲煙,回歸
驚醒
人遭逢重大傷痛時,心理會發動「刻意疏遠」或「自然遺忘」的功能以為保護,「冷漠」恰好透露「往昔錯過的用心」原有的熾熱。主人公曾試著以「冷漠」自我療癒,無奈事與願違,這些記憶總「化為季節雲煙,回歸」。「雲煙」可見而不可網羅,與記憶質性相似──非無非有、亦無亦有。第三行只有兩個字──「驚醒」,像樂譜上的表情記號,為這盤旋的意緒安上跳動的心律。
費了偌大工夫,楊牧才拋出三行,讓「風鈴」正式登場,「聲音」真相大白:
想像那是記憶
記憶的風鈴
大聲搖過我們的曾經
第二段:過份炫耀的展開部
第二段開頭,楊牧將莫大創造灌注於「傾斜的陽光如何運動」一事,空間高低、視角物我、節奏緩急,騰挪移轉。這是全詩最教人血脈賁張、氣管收縮的炫技段落。
秋之午後,當陽光試探了
水缸冷暖又將反影投射
天花板上,不斷波動
凝視一張喧嘩澌濺的床
「秋」和「午後」分別是一年、一日「高峰已過而終局未來」的過渡期,給人已沒法努力卻又不好放棄的「躊躇式徒勞」,點染慵倦疲憊的氣氛。「試探」則是面對未知、恐懼的一種警戒反應,這個擬人修辭,把波光粼粼的動態寫得物性、人情兩盡其妙;「試探冷暖」更把「重將往事思量過」的心情取象得十分熨貼,彷彿陽光之手簸搖了缸中淨水使之晃漾,為底下的「不斷波動」埋下伏索。舊憶、風、光、聲、鈴、水缸以及更後頭的大水(流、潭、洪),庶可看成是主人公之心不斷借殼、變形、換位的同質異態,那粼粼光影複誦著「我的心將不再平靜了」。
陽光射入水缸,乃由高向低;「又將反影投射/天花板上」,則低而復高。繼之,楊牧安排了一個定焦鏡頭:「不斷波動/凝視一張喧嘩澌濺的床」,結裹前行,陡然視角轉換,「凝視」一語換置了物我主客的對待關係,從「我看 光」翻作「光見我」,並帶出新的擺置──「床」(此即「睡」的變奏、「醒」的 伏兵)。「喧嘩澌濺」是波光而非床的質性,如此表述,則有光影又從天花板返照在床上的婉曲,又是一次由高向低的運動。這種起起伏伏的動態,象徵了不能平靜的心情。
我仰首默數光彩如潮
洶湧,在正上方變化
如暈,如雲,如星隕
依序升沉
第一行的「仰首」透露了主人公的位置與行為,只有位於低處才需「仰首」,而 光影的正下方便是「床」,由此可知主人公應是坐臥在床上。「光彩如潮」是「反影投射」、「不斷波動」的變奏,嚴守著意象連接著意象發展的結構技巧。「默數」有沉湎思量的意味,而「彩」字則給人奇崛不凡的想像;整句話有檢視心中舊憶何等奇崛的意思。楊牧接著抓準「洶湧」,連用三個意象,寫出先緩後疾的節奏──「如暈」,像油彩初滴入水中,中心濃而周圍淡,整體呈規律的圓形緩慢向外擴張;當擴張到臨界,圓形裂解,無方向地朝八方流散「如雲」;最後像「星隕」般飛速劃過。暈、雲、星「依序升沉」,形成如觀洪荒開闢般極隨機又極秩序的壯盛之美,這如潮光彩怎樣洶湧變化,便彷彿在目前了。
本段最終收在「如韻」二字,一方面表達光影、往事固有的情致(情韻)外,更重要的是完成「由光轉聲」的變換,亦即這個「韻」更多指涉了「聲韻」,也就是第一段所謂「輕巧的聲音」、「記憶的風鈴」,並攏絡了第三段的第一行「我聽到」。由第二段轉向三段,呈現了從光的運動到聲的運動之轉變。
第三段:開誠布公的再現部
第三段以「我聽到」承襲上一段的「如韻」,極力敷衍風鈴之聲如何運動。「跌宕」是一種不穩定的高低行進,這個動詞機巧地回應了前一段光影的上下騰挪,該模式再次讓人聯想起坎廩不平的心境。底下兩個障礙物乃脫胎於楊牧所深諳的《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綿》,其中「緜緜瓜瓞」成為後世子孫昌盛的題辭,而常語中又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表示事物的完成。故從懺情的角度解析,「收穫的瓜園」當是暗示對方婚姻的完成與發展,此即雖心繫之卻不得不「阻於圍牆」的癥結。此心受制於外在現實,已不容妄加探觸,正如鈴聲受物體阻絕而勢將反彈,「運動」由此持續:
遂反彈到半開的窗前
再不猶豫,飛踴到床上依偎
依偎著通紅的頰。
此「窗」既非暢行無阻的全開,也非閉籠深鎖的禁閉,「半開」反映的是徘徊可否之際的曖昧!然而既知瓜園有穫、圍牆阻隔,還存著可否之念,便可推想舊人舊事之可戀。但現實催促著理性發用,主人公毅然決然地「再不猶豫」,鈴聲從「半開的窗前」再「飛踴到床上依偎/依偎著通紅的頰」,由「窗-床-頰」,除了以空間轉移書寫主人公的思慮過程,更點明了他的位置與狀態──即「寤寐之間」。敻虹有詩曰:「不敢入詩的/來入夢/夢是一條絲/穿梭那不可能的相逢」,大概只有在夢的國度,人方能跨越阻隔,一親現實不能滿足的願望。頰所以「通紅」,可解作濃睡留下的紅印,也可說是思及舊夢所引發的赧然與激動,而作為下文的伏筆。「飄零/是髮,是惺忪的眼」乃睡眼惺忪、頭髮凌亂的描繪,更有力地支持了「寤寐之間」的推斷,而「飄零」則是對這個事件的直截論斷。楊牧既而就何以「通紅」大肆發揮,將想像從醒後回溯至夢中:
那音樂,這時,充滿了
亢奮的血管,一萬條支流
發源於夢的古潭,上下
頡頏,又一萬條支流
發源於夢的古潭
接觸,匯合
滂沛若洪水
在「夢的古潭」中,一切感覺、企望都得到昇華、放大,鈴聲變成了更複雜的「音樂」,並一變為磅礡的視覺摹寫──支流之數以萬計,血管亢奮,上下頡頏。頰的「通紅」顯示了潛意識的狂烈程度。在夢中,非但我可以想望她,甚至還自顧自地相信「我思君處君思我」,早已不得交接的彼此,竟可在夢中以同等的盛情「接觸,匯合/滂沛若洪水」。有多大的匱乏,便引發多強烈的補償欲望,主人公的心情始末,在第三段作出最不遮不掩的表白,將全詩推向未有的高峰。
第四段:尾聲
最末段,楊牧掇拾已用過的句子,從第一段「驚醒」後三行對幻聲真相的剖析,來到了第二段開頭的「秋之午後」。由主觀歸於恍若無情無感的外在客觀,以形式的復沓迴旋發揮了如戲劇收束的「疏離」作用,讓心由第三段的激昂回復平靜,張力獨具。而舊有的句子,又因一個「的」字之調動,使「我們的曾經」一變為「我們曾經的」,續以「秋之午後」,造成了欲說還休、不言而言的餘韻──「我們曾經的/秋之午後」內情如何呢?大抵「無非是往昔錯過的用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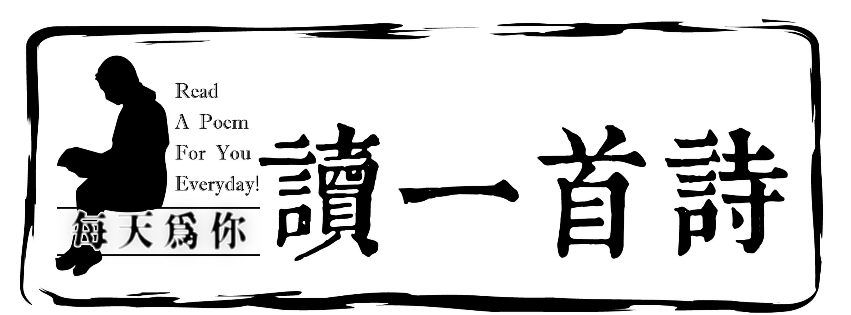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