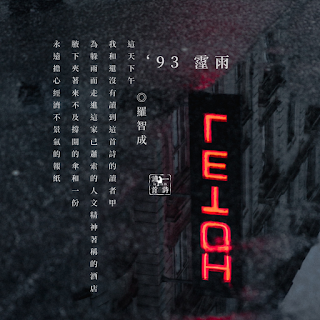前戲 ◎林宇軒
他是我認識世界的方法:「一起走嗎?
再也不要回來。」當我這麼問⠀⠀
──他的炭塗滿了我的生靈
光影在暗室流淌,洗劫我和他不堪的過往
本來面目,不過兩顆心乾乾淨淨
享受萬物在舌尖的雛形,嚐試
而敏於挺身。我一次次出神在此時
此地,一次次對床上的內臟下手,小小格局
來回製造動靜,嗯,他的確是個好人
有想法,刻苦耐勞,精明且知性
懂得去隱含一種堅持,能對誰
不帶齟齬地搬弄是非所以
我等。等的意思是選擇
知會的意思也是選擇⠀⠀
不愛是一種武器嗎?我提心上陣
無害的可能怯怯牴著骨架,直到完成自己
這些底細我全都記得。儘管只是剎那
誰的一部分曾死過,活過,在娑婆人世
我動用所有善感去揣摩
他,一個遲來的人開始認真
讓破破爛爛充盈身體,看我眼神迷離
裡頭多少個如此與當初,多少個我
為他漸次接受,直到彈指間大徹大悟:
眼。耳。鼻。舌。身。意外的浮屠
我展臂如兩面擦亮的鏡子
誰停下誰就是我的全部⠀⠀
對此我從不怪他。只感到空乏
人前人後我積累的時光
還不足對抗八方落下的水,一切的他
都使我精神抖擻,這麼多苦果與甜頭
成全我對他的體察:我願意如此
負責他的空前與絕後。當初所有執迷
驅使我兜手打勾,蓋印
誰能說自己沒有目的?我赫然抽身
受想行識,一心的疲沓
都來自他的過和我的不急
大千世界我告別當下的自己
只讓念頭在眼底掙扎──
而他說好。趁風雨正大
我們必須趕緊出發
-
◎作者簡介
林宇軒,1999年生,臺師大噴泉詩社顧問。國語日報專欄「詩的童話樂園」,著有詩集《泥盆紀》,Podcast節目《房藝厝詩》。
--
◎小編淵智賞析
*為方便讀者閱讀,若文中提及「我」,則是指詩中的第一人稱視角;若僅僅只是說我,而沒有引號,則代表小編的個人看法。造成閱讀上困擾還尚請海涵。
此首詩是宇軒於2021年獲得中興湖文學獎首獎的作品。宇軒素來擅於以事物間關係進行敘事,並在其中穿插對語言的實驗,如將「生靈塗炭」拆解成「他的炭塗滿了我的生靈」,「眼。舌。鼻。舌。身。意外的浮屠」六根中的「意」與「意外」的雙重意涵等等,由此種種可見他對於詩中意象與詞彙使用的挪移、轉換與連接之長,而這首〈前戲〉更是淋漓地展現了他的詩藝。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細讀這首詩吧。
從頭兩句開始:「他是我認識世界的方法:『一起走嗎?/再也不要回來。』當我這麼問」。此開頭便對於詩中的主要兩個人稱「我」與「他」之間的關係闡明了一簡單明瞭的定義。詩中的「他」,即是「我」與世界之間的橋樑,「我」必須經由「他」來認識這個世界,單單從首句,我們就可以隱約地感受到「我」與「他」之間的關係具有龐大的隱喻,不管是信仰上的貫連,或是任何情感上的糾葛,都足以見之。也正因為此複雜性藏得夠深,接下來的詩中,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在人稱之間的互動如何在詩人的意志中發揮效用。因此,接下來的問句也便順理成章的替此段關係的連袂進行開場,替整首詩開啟了理解與鋪敘之門:因著「我」對「他」依賴之深,一起出發便成了敘事者執著得近乎唯一的願求,而問出了如此深刻的一句告白:「一起走嗎?/再也不要回來。」——如此傾注全心全力渴望著的告白,此首詩的情調基礎大抵自此開始。
接著,來到次段,宇軒首次展現出了他所擅長的拆解詞彙功夫,將「生靈塗炭」拆成了「他的炭塗滿了我的生靈」,生靈在原成語中的涵義為「人民、百姓」,但拆開之後,所剩餘的詞彙「生靈」,在佛教道義中,也有著「活著的人靈魂出竅」之義,加上考慮到這首詩的兩個人稱互動之故,此一更動瞬間將原先成語的意義翻轉過來,原先的「炭」也從焚燒後的餘燼轉為正要起火的燃燒煤材。宇軒更以此意義的翻轉作為接下來句子的延續:「光影在暗室流淌,洗劫我和他不堪的過往」由炭的焚燒隱藏住火的隱喻,再以火焰所帶來的光影在暗室內製造的流動效果比擬為水,更以水的流動性將實際的物質轉換成抽象的人物關係之變化。我特別注意到了宇軒所使用的字眼為「洗劫」,如此一個負面性的詞彙,卻也在後面同樣負面的詞彙中,達成了負負得正的效果,彷彿屈原面臨汨羅江水,所說出的「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一般——當事物都淪陷於骯髒的境地時,就以不同的汙互相交迸,誕生出那些清朗的、出淤泥般的明亮——最終方得現出事物的本來面目。
而對宇軒來說,事物的本來面目,「不過是兩顆心乾乾淨淨/享受萬物在舌尖的雛形,嚐試/而敏於挺身」。布羅茨基曾說過「詩歌首先是一門關於指涉、暗示、語言相似性和形象相似性的藝術。」我們可以發現,在宇軒的詩中居然得以概括了這些詩歌的技巧,事物的本來面目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宇軒透過動作與名詞的實使得此一概念得以有所依附,讓我們知道事物的本來面目其實正正應當由我們心之錨點出發——只有當我們的心維持得夠乾淨時,才能得以共同感知到萬物,並且不斷地嘗試(當然,宇軒在這裡又玩弄了一個文字遊戲,將「嘗試」特別寫成「嚐試」,這固然是由於上句的舌尖所帶來的小樂趣)、運動與實踐,而這正正是詩歌指涉之所以始。回到最初我們曾討論過的「關係」,或許你會問,那這些跟詩中的「他」又有什麼關係呢?讓我先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再繼續往下來討論這首詩,而我認為,在談論關係間的密切時,我們更應當認知到所謂的關係,不過就是在談論心之間的互動與聯繫。
在此層面上,我們便可繼續往下理解詩中「我」的行動:「我一次次出神在此時/此地,一次次對床上的內臟下手,小小格局/來回製造動靜」,宇軒依然延續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詞彙使用,將「內臟」「下手」等極重且並非傳統美感性的字眼作為「我」如何去對於「他」進行認識:以內臟隱喻人的內裡,下手隱喻觸碰,本來看似是開膛剖腹的鮮豔視覺效果,卻被下面的「小小格局/來回製造動靜」而被收束起來,而讓整個動作被我們置於一個遠到足以欣賞的距離後面。由此隔開了讀者與「我」之間的距離,卻將「我」與「他」融會在一個心交神合的空間。這不但呼應了前面的「認識世界中的方法」一句中「我」與「世界」的距離,卻也替旁觀者帶來了視覺衝擊與意念的衝撞。
將讀者遠離了現場後,接下來,才正式地進入了「我」與「他」之間。
…...,嗯,他的確是個好人
有想法,刻苦耐勞,精明且知性
懂得去隱含一種堅持,能對誰
不帶齟齬地搬弄是非所以
我等。等的意思是選擇
知會的意思也是選擇
透過「我」的眼睛,我們看得見他的種種優點,無論是有想法、刻苦耐勞,這種意志上的指向,正正昭顯出了「我」對於「他」的傾慕,使得「我」在一種情境下,願意去等待他,那這樣的情境是什麼情境呢?回到詩的開頭,或許你還記得,「我」曾經問出了一個問題:「一起走嗎?/再也不要回來。」當一個問題之發生,其所期待的必然是一個答案,但詩行至此,我們卻依然沒看到回答,在「我」內心中之焦急便油然而生。「我」便這樣開始進行了自我傾訴——究竟他有什麼優點,值得我為他等候?因此,我們便看到了這樣一個自我說服的過程:等待著「他的選擇」。這裡所隱藏的小小心思不由得使我感受到一種戀愛般的青澀感覺,只為了對方的選擇而苦苦等候著。
正因為這種少年情思所帶來的苦悶與糾結,下一段關於愛的辯證邏輯便因而順勢誕生。
不愛是一種武器嗎?我提心上陣
無害的可能怯怯牴著骨架,直到完成自己
這些底細我全都記得
在「我」與「他」的關係尚未確立與認證以前,兩人之間竟恍如戰場一般,「我」用心來抵抗著你的「不愛」,並在不斷抗拮的過程中,重新完成「我」在有他的世界裡應有的自我姿態,也使得兩人之間的所有情節與底細,都在這樣一場戰役中不斷地被記起。因此,「我」也終於開始思考起自我的姿態。而在閱讀這首詩的同時,我卻也透過了「我」的眼睛,參與了這場戰役一樣,感受到那些「他」的崇高、知性,彷彿一切我們所欲追尋之事物,彷彿我作為一個讀者,卻也已經替這個「他」找到了他的身分,不管是愛情、真理,還是知識——我終於在這首詩裡看到了詩的最基本姿態:「詩不過就是一種簡單的常識」,展現出了一個主體對客體之間的追尋與自我形體之確立。
接下來,宇軒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終於開始摸索起「我」的型態,「一個遲來的人開始認真/讓破破爛爛充盈身體,看我眼神迷離/裡頭多少個如此與當初,多少個我/為他漸次接受,直到彈指間大徹大悟」。「我」作為一個「遲來的人」,開始試圖充盈著自己的身心與靈魂,重新見識到最初的本我,從而能夠被他接受。閱讀至此,我不禁在想,究竟「我」的「遲來」是指什麼呢?接著我便想起了上面的句子「無害的可能怯怯牴著骨架,直到完成自己」,我突然領悟到了,或許那些遲來的部分,便是那些在無「他」的世界中,飄零四散的自我的破爛碎片,因為想要配合他的完整,而像磁鐵一般重新依附回「我」的身體,從而逐漸完整成一個足以配上「他」的「我」。而下面的句子卻也證實了我的想法:
眼。耳。鼻。舌。身。意外的浮屠
我展臂如兩面擦亮的鏡子
誰停下誰就是我的全部
眼、耳、鼻、舌、身、意的原典也是來自佛教用語,本是指六個感官器官,但卻在上面的詩句中被視為自我零碎部分的具體展現,我們方又得以發現這是宇軒的所擅長的技巧:拆解語言的原義,並重新依附上自己的詩感。而六根最後一根的「意」,卻也因為下面所接的一個「外」字而產生了新義,除了「意」之「外」的意涵之外,也有了「意外」的意涵。此一意外又是因何而來呢?閱讀時我依然思索到了這個問題,最後我給自己的一個答案是「他的出現」,或許對「我」而言是一種奇蹟,但奇蹟背後所隱隱顯現地,更是一種意外——只有當我們發生了意料之外的幸事時,我們才會將之稱為奇蹟。
但這種奇蹟的煥發,才得以使得「我」在追尋的過程中,重新找回自我,在這段末尾,「我」所展現的姿態,卻竟然與「他」之間有所翻轉,從原先的可望依附,成了一種救贖者的姿態:「我展臂如兩面鏡子/誰停下誰就是我的全部」,這樣一個宣言,讓我們得以看見原先破爛的「我」,在這樣的一個關係追尋過程裡,漸漸對於自己的一切明朗,也知道了究竟什麼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一切姿態都被濃縮在一顆明亮的心,張開雙臂便能擁抱住一切。
但即使自我已然完成至此,「他」卻依然沒有回應,對此「我」終於也感到空乏,終於寫下了下一段的開始「對此我從不怪他。只感到空乏/人前人後我積累的時光/還不足對抗八方落下的水」,我彷彿感受得到「我」的那種疲倦——那些一再地積累、枯等的日子,以及在努力之後,隨之迎來的更洶湧的落下的水。然而,正當我們以為「我」就要如此放棄時,宇軒卻寫下了「我」在面對這些苦難時所隱含的堅持——那種隱含的堅持終於不僅僅只是在「他」身上發生,而是透過這些歷練,使得「我」漸漸成為一個像「他」這樣的一個趨近完人的人。也正因如此,「我」作出了我的宣言:「我願意如此/負責他的空前與絕後」這樣一個告白也替「我」自己找到了新的起點,在說出了「我願意」之後,所有事物與誓約,終於可以重新開始重新被自身所檢視,不管是在「他」與「我」之間,還是「我」在前進時,如何去一次又一次得完整自身。我終於得以見證到了「我」來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一個學會向當下的自己告別的「我」、一個學會只讓自己意志主導身體、靈魂運行的「我」。
或許這樣的改變,終於也使得「他」看見了吧,因此,從開頭時,我們便不斷地在等待著的答案,終於在詩的最末出口了:「而他說好。」我想,這樣短短一個字,或許卻是詩中的「我」歷經了千百劫難之後,所得到的一個最完整的答案了。
--
美術設計:吳浩瑋
--
#林宇軒 #暑假無主題詩選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